历代医籍并无瘀毒之名,而名瘀血、恶血、蓄血、血瘀者,常含瘀毒之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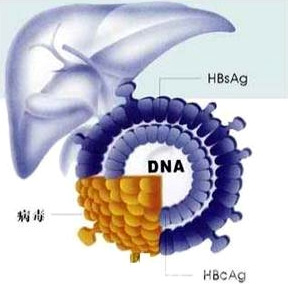 中医学对“瘀”的论述很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,目前我国很古老的医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就有关于活血化瘀法治疗“蛊”病的记载。《武威汉代医简》,简牍共92枚,其中记载活血化瘀治法的就有9枚。简文中所载治“瘀”的具体方药体现了对后来中医学中“气为血帅,血为气母”理论的具体运用。对于久瘀之患则以活血化瘀峻药——虫类药物搜剔络道,增强通经活络作用,显示了其治法用药上的多样性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虽无瘀血一词,但有“血凝涩”、“血脉凝泣”、“脉不通”、“恶血”、“留血”、“血著”等30余种近似瘀血名称的记载,并在一些篇章里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及瘀血导致的症状。在治疗上,《黄帝内经》指出了以疏决通导为主的基本治疗原则,如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:“血实宜决之”,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指出:“疏其血气,令其调达,而致和平”,“坚者消之”、“结者散之”、“留者攻之”。《素问汤液醪醴论》曰:“去宛陈莝”。《灵枢小针解》曰:“宛陈则除之者,去血脉也。”以上可以认为是活血化瘀治法的理论雏形,形成了活血化瘀的基本概念,从而为后世医家研究发展活血化瘀理论、创制活血化瘀方药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中医学对“瘀”的论述很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,目前我国很古老的医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就有关于活血化瘀法治疗“蛊”病的记载。《武威汉代医简》,简牍共92枚,其中记载活血化瘀治法的就有9枚。简文中所载治“瘀”的具体方药体现了对后来中医学中“气为血帅,血为气母”理论的具体运用。对于久瘀之患则以活血化瘀峻药——虫类药物搜剔络道,增强通经活络作用,显示了其治法用药上的多样性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虽无瘀血一词,但有“血凝涩”、“血脉凝泣”、“脉不通”、“恶血”、“留血”、“血著”等30余种近似瘀血名称的记载,并在一些篇章里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及瘀血导致的症状。在治疗上,《黄帝内经》指出了以疏决通导为主的基本治疗原则,如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:“血实宜决之”,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指出:“疏其血气,令其调达,而致和平”,“坚者消之”、“结者散之”、“留者攻之”。《素问汤液醪醴论》曰:“去宛陈莝”。《灵枢小针解》曰:“宛陈则除之者,去血脉也。”以上可以认为是活血化瘀治法的理论雏形,形成了活血化瘀的基本概念,从而为后世医家研究发展活血化瘀理论、创制活血化瘀方药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中医学对于“毒”的很早记载亦当属《五十二病方》,除“蛊”病的记载外,另有两处治疗箭毒的处方。《黄帝内经》对“毒”的论述多达34处,主要论述了病因之毒和药物之毒。病因之毒首次提出了寒毒、热毒、湿毒、清毒、燥毒、大风苛毒的概念,如《素问生气通天论》:“虽有大风苛毒,弗之能害”。对于外来感染性致病毒邪,《黄帝内经》中称之为“疠”。关于药物之毒的论述,有的指药物,有的指药物的偏性与峻烈性,如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:“有毒无毒,所治为主。”《素问异法方宜论》:“其病生于内,其治宜毒药。”《素问五常政大论》:“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;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。”《素问?移精变气论》:“今世治病,毒药治其内,针石治其外”。
汉代张仲景是血瘀理论的奠基人。他在《金匮要略-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》中总结前人经验,首先提出了“瘀血”这个名称,并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科疾病,开后世瘀血证之先河。久病入络,瘀血内阻,加重病情,治当活血化瘀。并在治疗蓄血、血痹、虚劳、癥瘕、产后腹痛等疾病中,叙述了瘀血的几种主要症状及脉象,且在其他篇章中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和治疗。在《伤寒论》的“辨太阳病脉证并治”和“辨阳明病脉证并治”中,对血瘀证作了较详细的阐述,制定了桂枝茯苓丸、下瘀血汤、桃仁承气汤、抵当汤、鳖甲煎丸、大黄zaozi001虫丸、旋覆花汤、温经汤、当归芍药散等方剂。张仲景所用活血化瘀诸方,可谓用药精当,法度严谨,配伍巧妙,旨在使“五脏元真通畅,人即安和”。其指导临床遣药组方意义深远,开拓了杂病、伤寒和妇科瘀血论治的新领域,为后世应用活血化瘀药树立了典范。
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》中根据证候的属性把毒邪分为阳毒和阴毒,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阳毒、阴毒致病的症状、预后及证治方药,对后世颇有启发。晋代王叔和《伤寒例》在继承《黄帝内经》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的理论基础上,提出“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”的伏寒化温说,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。
特别应当指出的是,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其所著《中藏经》中提出“蓄毒”致病的观点:“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,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,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。”发展了《黄帝内经》以来关于肿瘤病因的学说,开创了“癌症瘀毒论”之先河(注:亦有学者认为《中藏经》为六朝人所作,托名华佗)。
汉晋之后,经过唐宋以至金元时代,瘀证及毒邪的论述在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。隋唐时代,如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书,将瘀血作为一个证候,并在有关疾病如血证、积聚的病机中阐述,使活血化瘀治则在理论、方剂、药物等方面更加完善。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以仲景桃仁承气汤、抵当汤为基础加减化裁出治妇女月经不通的桃仁汤、芒硝汤、桃仁煎,并以仲景大黄zaozi001虫丸加减化裁出桂心酒方,用治妇女月经不通,结成癥瘕。宋元时代,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对于“产后心腹痛欲死,百药不救”者,以药性平和、善能活血化瘀止痛的五灵脂与蒲黄同用,组成失笑散一方。由于该方有良好的化瘀止痛之功,故后世对其运用有较大的发展。朱丹溪重视解郁散结,创立气、血、湿、痰、食、热六郁之说,其中以气血之郁尤为重要。他认为“气血冲和,万病不生,一有怫郁,诸病生焉”。他所谓的郁,可看做是血瘀的早期或轻症。
隋代巢元方在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说:“恶核者……风邪挟毒所成”,进一步丰富了肿瘤的毒邪致病学说。《诸病源候论》“腕伤病诸候”、“妇人杂病诸候”、“妇人妊娠病诸候”、“妇人产后病诸候”各篇中详论瘀证的同时,根据毒邪性质及来源不同,结合证候表现,对毒邪进行命名,并对其所致疾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,使瘀、毒致病的理论得到发展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引用《小品方》认为“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”,其中“犀角地黄汤,治伤寒及温病,应发汗而不汗之,内有蓄血者,及鼻衄吐血不尽,内有瘀血,面黄,大便黑,消瘀血方。”此方后来成为祛瘀生新、凉血解毒的名方。《外台秘要》对活血化瘀方有了更多论述,如从高坠下瘀血及折伤内治方16首、折腕瘀血方4首等。另外,《外台秘要》还对“热毒”所致疾病进行了详细论述,如“若热毒在胃外,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,其热乘虚便入胃,则烂胃也”,还列举了若干毒物致病及解毒方药。
金元时代是中医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,涌现了如著名的“金元四大家”等医家,各医家对“瘀”、“毒”致病及治疗均做了深入探讨。刘河间、张从正治疗疾病都以解毒攻邪著称。刘河间在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,从理论上揭示了火热致病的病变机制。张从正倡导“攻邪”治法,提出“先论攻其邪,邪去而元气自复”的新观点,为后世“热毒”相关疾病的解毒祛邪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庞安时所著《伤寒总病论》,在王叔和“寒毒”学说的基础上,认为患者的体质与“阴毒”或“阳毒”的发病密切相关,如“凡人禀气各有盛衰,宿病各有寒热。假令素有寒者,多变阳虚阴盛之疾,或变阴毒也;素有热者,多变阳盛阴虚之疾,或变阳毒也”,并对犀角地黄汤治疗“内热瘀血”的治疗结果给予了肯定。
明清至民国时期,随着医学的发展,形成了比较系统的“瘀”、“毒”致病理论体系。人们对瘀血的认识不断深入,使活血化瘀治法日益发展与完善。如明代朱zaozi002等编的《普济方》,已注意到瘀血的危害,该书“诸血门”谓:“人之一身不离乎气血,凡病经多日治疗不愈,须当为之调血……用药川芎、莪术、桃仁、灵脂、生地、大黄为要,呕甚者多加生姜,以此先利诸瘀。”《景岳全书》详细论述了血瘀证的用药,如“血有蓄而结之,宜破之逐之,以桃仁、红花、苏木、玄胡、三棱、蓬术、五灵脂、大黄、芒硝之属”,“血有涩者,宜利之,以牛膝、车前……木通……益母草……之属”,“血有虚而滞者,宜补之活之,以当归、牛膝、川芎、熟地、醇酒之属”等,认为“补血行血无如当归”,“行血散血无如川芎”;同时指出,治疗“热毒之痛”应“以寒凉之药折其热,而痛自止也”。清代,血瘀学说有了较大的发展,其中叶天士、王清任、唐容川三位医家,对此作出较大贡献。叶天士认为初病在经,久病入络,“经主气,络主血,久病血瘀”,提出“久病入络”的理论,倡导“通络”之说。他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一书中,对痹证、郁证、积证、癥瘕、疟母、噎膈、便秘及月经胎产等多种病证,广泛应用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药物,对瘀血严重及有干血内结者,还常使用蜣螂、水蛭等虫类逐瘀药。叶天士治疗出血病,提出“入血尤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”之观点,对近世治疗出血病证,如弥漫性出血、流行性脑炎败血症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应用清热凉血化瘀之法,颇有指导意义。至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对活血化瘀治法尤有心得,创制了诸多良方,从而使活血化瘀方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。在王清任所创活血方中,有代表性的当为“五逐瘀汤”——血府逐瘀汤、通窍活血汤、膈下逐瘀汤、少腹逐瘀汤、身痛逐瘀汤。这些方药为后世医家临床治疗瘀血病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王清任对瘀血证治的另一重大贡献,是其所创制的体现气虚血瘀理论的代表方剂补阳还五汤。王清任对于中风半身不遂的病机,首次提出是元气亏损、半身无气的结合,认为“元气既虚,必不能达于血管,血管无气,必停留而瘀”。根据其“气虚血瘀”理论,将补气与活血化瘀合用,从而创制了益气活血通络的补阳还五汤,开创了补气法治疗中风的先河。王清任在丰富了补气活血和祛瘀活血等治法的同时,对因毒致瘀进行了阐述。他在《医林改错》中说:“温毒在内烧炼其血,血受烧炼,其血必凝”。据统计,《医林改错》中以活血化瘀为主的方剂有33首,主治各类瘀血病证50余种,并创立了“活血解毒汤”以治疗“瘟毒吐泻转筋”。继王清任之后,唐容川对瘀血学说也有较大的贡献。他所著的《血证论》详述了各种出血证的证治:同时,阐明了瘀血和出血之间的关系,把消瘀作为活血四法之一:并认为祛瘀与生新有着辩证关系:主张“凡吐血、衄血,不论清、凝、鲜、黑总以祛瘀为先”,大大地扩大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范围。
明清时期毒邪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。明代吴又可《温疫论》提出了“杂气说”,使毒邪的含义进一步明确,即“毒”不仅指六淫之甚,还包括六淫之外的一些特殊致病因素。明代董宿辑录《奇效良方》云:“毒气自脏里而达外,治之要法,但活血解毒而已”,孟继孔《幼幼集》亦曰:“内毒太盛,疮必稠密,急宜投以解毒活血、消导清凉之剂”,并以活血解毒汤治疗痘后余毒。近代医家张锡纯对王清任活血化瘀治法颇有研究和体会,其创制的活络效灵丹(当归、丹参、乳香、没药)为后世广为应用。张锡纯所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还记载了他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病案。鲍相璈《验方新编》对“毒瘀”的致病特点进行了论述,如“毒瘀肝经,损坏内溃,吐血数发,势极多危。毒瘀心包络,更加凶险,不待时日”,说明“瘀毒”对于心脏的影响尤为严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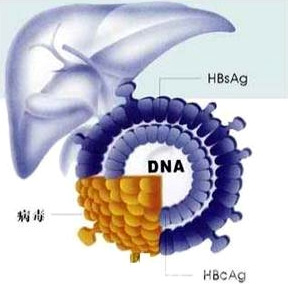
中医学对于“毒”的很早记载亦当属《五十二病方》,除“蛊”病的记载外,另有两处治疗箭毒的处方。《黄帝内经》对“毒”的论述多达34处,主要论述了病因之毒和药物之毒。病因之毒首次提出了寒毒、热毒、湿毒、清毒、燥毒、大风苛毒的概念,如《素问生气通天论》:“虽有大风苛毒,弗之能害”。对于外来感染性致病毒邪,《黄帝内经》中称之为“疠”。关于药物之毒的论述,有的指药物,有的指药物的偏性与峻烈性,如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:“有毒无毒,所治为主。”《素问异法方宜论》:“其病生于内,其治宜毒药。”《素问五常政大论》:“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;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。”《素问?移精变气论》:“今世治病,毒药治其内,针石治其外”。
汉代张仲景是血瘀理论的奠基人。他在《金匮要略-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》中总结前人经验,首先提出了“瘀血”这个名称,并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科疾病,开后世瘀血证之先河。久病入络,瘀血内阻,加重病情,治当活血化瘀。并在治疗蓄血、血痹、虚劳、癥瘕、产后腹痛等疾病中,叙述了瘀血的几种主要症状及脉象,且在其他篇章中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和治疗。在《伤寒论》的“辨太阳病脉证并治”和“辨阳明病脉证并治”中,对血瘀证作了较详细的阐述,制定了桂枝茯苓丸、下瘀血汤、桃仁承气汤、抵当汤、鳖甲煎丸、大黄zaozi001虫丸、旋覆花汤、温经汤、当归芍药散等方剂。张仲景所用活血化瘀诸方,可谓用药精当,法度严谨,配伍巧妙,旨在使“五脏元真通畅,人即安和”。其指导临床遣药组方意义深远,开拓了杂病、伤寒和妇科瘀血论治的新领域,为后世应用活血化瘀药树立了典范。
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》中根据证候的属性把毒邪分为阳毒和阴毒,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阳毒、阴毒致病的症状、预后及证治方药,对后世颇有启发。晋代王叔和《伤寒例》在继承《黄帝内经》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的理论基础上,提出“寒毒藏于肌肤,至春变为温病”的伏寒化温说,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。
特别应当指出的是,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其所著《中藏经》中提出“蓄毒”致病的观点:“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,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,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。”发展了《黄帝内经》以来关于肿瘤病因的学说,开创了“癌症瘀毒论”之先河(注:亦有学者认为《中藏经》为六朝人所作,托名华佗)。
汉晋之后,经过唐宋以至金元时代,瘀证及毒邪的论述在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。隋唐时代,如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书,将瘀血作为一个证候,并在有关疾病如血证、积聚的病机中阐述,使活血化瘀治则在理论、方剂、药物等方面更加完善。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以仲景桃仁承气汤、抵当汤为基础加减化裁出治妇女月经不通的桃仁汤、芒硝汤、桃仁煎,并以仲景大黄zaozi001虫丸加减化裁出桂心酒方,用治妇女月经不通,结成癥瘕。宋元时代,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对于“产后心腹痛欲死,百药不救”者,以药性平和、善能活血化瘀止痛的五灵脂与蒲黄同用,组成失笑散一方。由于该方有良好的化瘀止痛之功,故后世对其运用有较大的发展。朱丹溪重视解郁散结,创立气、血、湿、痰、食、热六郁之说,其中以气血之郁尤为重要。他认为“气血冲和,万病不生,一有怫郁,诸病生焉”。他所谓的郁,可看做是血瘀的早期或轻症。
隋代巢元方在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说:“恶核者……风邪挟毒所成”,进一步丰富了肿瘤的毒邪致病学说。《诸病源候论》“腕伤病诸候”、“妇人杂病诸候”、“妇人妊娠病诸候”、“妇人产后病诸候”各篇中详论瘀证的同时,根据毒邪性质及来源不同,结合证候表现,对毒邪进行命名,并对其所致疾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,使瘀、毒致病的理论得到发展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引用《小品方》认为“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”,其中“犀角地黄汤,治伤寒及温病,应发汗而不汗之,内有蓄血者,及鼻衄吐血不尽,内有瘀血,面黄,大便黑,消瘀血方。”此方后来成为祛瘀生新、凉血解毒的名方。《外台秘要》对活血化瘀方有了更多论述,如从高坠下瘀血及折伤内治方16首、折腕瘀血方4首等。另外,《外台秘要》还对“热毒”所致疾病进行了详细论述,如“若热毒在胃外,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,其热乘虚便入胃,则烂胃也”,还列举了若干毒物致病及解毒方药。
金元时代是中医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,涌现了如著名的“金元四大家”等医家,各医家对“瘀”、“毒”致病及治疗均做了深入探讨。刘河间、张从正治疗疾病都以解毒攻邪著称。刘河间在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,从理论上揭示了火热致病的病变机制。张从正倡导“攻邪”治法,提出“先论攻其邪,邪去而元气自复”的新观点,为后世“热毒”相关疾病的解毒祛邪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庞安时所著《伤寒总病论》,在王叔和“寒毒”学说的基础上,认为患者的体质与“阴毒”或“阳毒”的发病密切相关,如“凡人禀气各有盛衰,宿病各有寒热。假令素有寒者,多变阳虚阴盛之疾,或变阴毒也;素有热者,多变阳盛阴虚之疾,或变阳毒也”,并对犀角地黄汤治疗“内热瘀血”的治疗结果给予了肯定。
明清至民国时期,随着医学的发展,形成了比较系统的“瘀”、“毒”致病理论体系。人们对瘀血的认识不断深入,使活血化瘀治法日益发展与完善。如明代朱zaozi002等编的《普济方》,已注意到瘀血的危害,该书“诸血门”谓:“人之一身不离乎气血,凡病经多日治疗不愈,须当为之调血……用药川芎、莪术、桃仁、灵脂、生地、大黄为要,呕甚者多加生姜,以此先利诸瘀。”《景岳全书》详细论述了血瘀证的用药,如“血有蓄而结之,宜破之逐之,以桃仁、红花、苏木、玄胡、三棱、蓬术、五灵脂、大黄、芒硝之属”,“血有涩者,宜利之,以牛膝、车前……木通……益母草……之属”,“血有虚而滞者,宜补之活之,以当归、牛膝、川芎、熟地、醇酒之属”等,认为“补血行血无如当归”,“行血散血无如川芎”;同时指出,治疗“热毒之痛”应“以寒凉之药折其热,而痛自止也”。清代,血瘀学说有了较大的发展,其中叶天士、王清任、唐容川三位医家,对此作出较大贡献。叶天士认为初病在经,久病入络,“经主气,络主血,久病血瘀”,提出“久病入络”的理论,倡导“通络”之说。他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一书中,对痹证、郁证、积证、癥瘕、疟母、噎膈、便秘及月经胎产等多种病证,广泛应用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药物,对瘀血严重及有干血内结者,还常使用蜣螂、水蛭等虫类逐瘀药。叶天士治疗出血病,提出“入血尤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”之观点,对近世治疗出血病证,如弥漫性出血、流行性脑炎败血症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应用清热凉血化瘀之法,颇有指导意义。至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对活血化瘀治法尤有心得,创制了诸多良方,从而使活血化瘀方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。在王清任所创活血方中,有代表性的当为“五逐瘀汤”——血府逐瘀汤、通窍活血汤、膈下逐瘀汤、少腹逐瘀汤、身痛逐瘀汤。这些方药为后世医家临床治疗瘀血病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王清任对瘀血证治的另一重大贡献,是其所创制的体现气虚血瘀理论的代表方剂补阳还五汤。王清任对于中风半身不遂的病机,首次提出是元气亏损、半身无气的结合,认为“元气既虚,必不能达于血管,血管无气,必停留而瘀”。根据其“气虚血瘀”理论,将补气与活血化瘀合用,从而创制了益气活血通络的补阳还五汤,开创了补气法治疗中风的先河。王清任在丰富了补气活血和祛瘀活血等治法的同时,对因毒致瘀进行了阐述。他在《医林改错》中说:“温毒在内烧炼其血,血受烧炼,其血必凝”。据统计,《医林改错》中以活血化瘀为主的方剂有33首,主治各类瘀血病证50余种,并创立了“活血解毒汤”以治疗“瘟毒吐泻转筋”。继王清任之后,唐容川对瘀血学说也有较大的贡献。他所著的《血证论》详述了各种出血证的证治:同时,阐明了瘀血和出血之间的关系,把消瘀作为活血四法之一:并认为祛瘀与生新有着辩证关系:主张“凡吐血、衄血,不论清、凝、鲜、黑总以祛瘀为先”,大大地扩大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范围。
明清时期毒邪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。明代吴又可《温疫论》提出了“杂气说”,使毒邪的含义进一步明确,即“毒”不仅指六淫之甚,还包括六淫之外的一些特殊致病因素。明代董宿辑录《奇效良方》云:“毒气自脏里而达外,治之要法,但活血解毒而已”,孟继孔《幼幼集》亦曰:“内毒太盛,疮必稠密,急宜投以解毒活血、消导清凉之剂”,并以活血解毒汤治疗痘后余毒。近代医家张锡纯对王清任活血化瘀治法颇有研究和体会,其创制的活络效灵丹(当归、丹参、乳香、没药)为后世广为应用。张锡纯所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还记载了他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病案。鲍相璈《验方新编》对“毒瘀”的致病特点进行了论述,如“毒瘀肝经,损坏内溃,吐血数发,势极多危。毒瘀心包络,更加凶险,不待时日”,说明“瘀毒”对于心脏的影响尤为严重。
* 温馨提示:本院案例真实有效,只供业内专业人士研究使用,不作为用药指导和对患者的承诺保障。
上一篇:肝癌瘀毒论的概念 下一篇:现代医家对肝癌瘀毒的研究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